一年以后,当克利夫兰孤身一人面对整个深海舰队的舰炮时,她也会想到那个和海伦娜一起在港口附近山上看烟花的夜晚。
总算是放假了克利夫兰一脸疲态地倒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喃喃自语。
她坐了起来,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上写满了以往从没有过的疲倦。他不知道自己最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即使是在与女友海伦娜冷战中,她觉得也不应该是这样:反正她就是这样一直闷闷不乐的人,虽不至于像亚利桑那和朱诺一样整天哭哭啼啼,但也不是像自己那般的乐天派。不开心又能怎么样呢?总不至于分手吧。
海伦娜坐在靠窗的上,进门右手边坐着伊丽莎白女王和厌战,贝尔法斯特在旁边装模作样地给女王倒红茶。大黄蜂还是像往常一样地吵,旁边的企业皱着眉头看着妹妹。威尔士和欧根——
等等,为什么她们两个会在一起?!还有胡德去哪了?伴随着小海狸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的聒噪声,克利夫兰的脑袋感觉要炸掉了。
先不去想这种无聊的事情,当务之急是跟海伦娜说自己要约她找个时间出来谈谈。克利夫兰深吸了一口气,走到了海伦娜的座位边上,抽出凳子坐了下来。
胡德要是在这里,是不是也会变成那边的气氛呢?欧根倒是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这种奇妙的局面。不过威尔士你为什么要往我的全麦面包上抹果酱?
明天下午两点,学院的后山见。几乎是低声下气似的,克利夫兰在海伦娜错过去的一瞬间,低声嘟哝着。
克利夫兰晃了晃脑袋,现在自己必须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去应战。她粗略看了一下,对方大约有三艘战列舰,七艘巡洋舰,以及十艘和两艘航母,而自己这边,只有她一人。
克利夫兰,克利夫兰,规避失败,请把信号端交给海伦娜,再重复一遍,规避失败,请把信号端交给海伦娜。克利夫兰额头上冒着细密的汗珠,她知道这一次,可能真的结束了。
第二天克利夫兰如同约定的那样去了学院的后山,这里并不是什么乡村,而是真正的野外——来自港区燥热的蔓延而上,走到这里,仿佛是走到了尽头。远处是群山的褶皱,的草地在山脚下铺开,其中点缀着白色的小花和大叶草,一座又一座的小山丘在眼前起伏着,夕阳撒到小山包,晚风吹动着雨后的青草,空气中弥漫着寂静的味道。
克利夫兰知道海伦娜几乎是不会来了,但不知道怎地,她内心中还存有一点点小小的期望——当了海伦娜好多年恋人的她至少认为,事情还没有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你连自己错在哪里都不知道,还怎么跟我谈?唔猝不及防,克利夫兰地吻上了海伦娜,无论她怎样挣扎,捶打,她都没有要松开的意思。
每次都这样把事情糊弄过去,我要生气了!海伦娜被吻得脱了力气,倚靠在克利夫兰的怀里,满脸不高兴地说道,说完还没忘不轻不重地朝着克利夫兰的胸口打了一下。
她们牵着手走在这片茫茫的山下草原上,耳边只有风声,或许还有一两声从远处传来的动物叫声,让人希望这一刻不要有别的声音出现,当然更不要有人说话。任何音乐也比不上这种声音。它让人轻松愉悦,思绪飞向不知何方。
午后的温度太高,注定没有什么人愿意出来。然而这是恋人们活跃的时段,炎热的时段晒得人发晕,促进盲目的热情,以此愉悦自己。恋人们不是老人,不会甘心在这样的时段里整日睡眠。
克利夫兰歪歪扭扭地打了海伦娜一下,笑嘻嘻地跑开了,海伦娜也笑着追了上去。在休息时,她们看到一座陡峭的山包。在她们看来那不能算陡峭,简直就是无语自明的地标。
她们以为这样就可以踩出一条。可一松脚,这些草就又弹了起来。她们陷进了一片野草的迷宫。极缓慢地着。视线所及,越是野草高而茂密。费尽全力也没有走出很远。克利夫兰有些后悔,刚准备抱怨,海伦娜停住了。
湖静静地泛着涟漪。整个湖在群山的环抱之下,整个山脉包着一片湖,不翻越山脉便无法看到的湖,而那陡峭的山包,正是最矮的一节。云絮如牛奶般点如其中。化开。湖上的青草是天空与湖面的现实连接点。
湖是活水,没有浮萍。入水口狭小,出水口也同样。青草从入水口进来,又从出水口汇入一条溪流出。它们在湖面静静盘旋,在湖中心周围形成巨大而和缓的浅漩。吸引了所有注意力。之后这漩涡的底端又生出曲线波纹,顺出水口向去。漂浮的草团在出水口与入水口相互碰撞,无法控制它们由上自下的流向。
远处起了一阵风,风声在这山中间湖中心回响。她俩回过神来,欢叫一声,冲向湖边。边跑边扯下身上的衣物。踏入水里。
海伦娜尖声叫着避开了,回击。克利夫兰迎着水花,抓住她的手臂,横抱起来,丢在湖里。她们游了好一会。直到海伦娜抵抗着,笑着,被克利夫兰剥下仅剩的所有衣服。
日落时她们累了,仰面倒在湖边的草地。克利夫兰坐了起来,熔金的光缓缓倾倒,自己的影子渐渐拉长。
克利夫兰看着影子越过湖畔的分割线,切割湖畔的细石,吞吃着海伦娜的水蓝色的头发,纤细的手臂,的肚脐,修长的脚趾。
她不由自主地翻身压到了海伦娜的身上——除却恼人黏腻的汗液,这里不会碰见一个熟人,夏天来的正是时候。
现在即使身上挂满sg雷达也没有用了吧?她苦笑道,刚才她就感到大局已定,她现在只想多听听海伦娜的声音。
啊!突如其来的疼痛让克利夫兰几乎昏了过去,自己的左臂被一颗炮弹完全炸烂了,她感到血在呼哧呼哧地从她体内流走,失血带来的强烈的疲惫感让她的步伐开始变得踉跄。
天色已晚,刚才克利夫兰和她云雨过后,手上还粘着她的体液,现在的她一丝不挂地坐在自己边上,但丝毫没有刚才放荡的感觉,借着湖面反射的微弱天光,克利夫兰隐约看到,她像圣母一样,平静,,一种名叫幸福的辉光着她。
克利夫兰坐了起来,背对,自己不去看海伦娜。她感到海伦娜从自己背后抱了上来,海伦娜纤细的睫毛一遍一遍刷着自己的后背。
你在干什么呀克利夫兰感到一阵害羞,这是她第一次来这个港区报道,对海伦娜说的话。
但是但是你能不能多想一下我?海伦娜声音越来越小,克利夫兰感觉得到自己的后背上两股湿热的暖流。
头好痛,脑袋里已经记不得当时海伦娜说了什么,只有零星几句模糊的话语在脑海里不断回荡着。刚才又有一颗炮弹打断了克利夫兰的右腿胫骨,她可以感到自己在慢慢地沉入水中。
克利夫兰没有说话,看着远处,不一会儿,她开口:我已经差不多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了,时间过得真快啊,我想,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一个人了,所以她顿了顿。
所以,我克利夫兰的生命不再是属于我一个人和这个港区,它同样也全部属于你,海伦娜。克利夫兰转过头来,其事地说道。
克利夫兰!克利夫兰!你给我回答啊克利夫兰!给我活着啊!你给我说句话啊!通讯器里的海伦娜带着哭腔喊着。
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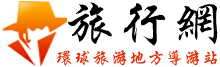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