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大克利夫兰联合劝募协会(the United Way of Greater Cleveland)向大气层中放了近150个氦气球,以此这座城市,筹集资金,以及打破一项世界纪录。当大量的五彩乳胶如奇妙的椋鸟群般飞空时,围观者们无不为之欢呼。在开始飞散之前,它们吞没了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物——终端塔。不过天气状况很快发生了变化,这些充气气球从天而降,它们慢慢如雨点般落在城市里,仿佛之火的滑稽版。这些气球被认作是导致两位渔民死亡的原因,因为对他们的搜寻受到了落在伊利湖水域的成千上万的气球的阻碍。
据说,这一气球噱头花了50万美元来筹备。这场表演也是一个正在萎缩的城市对于正向关注所发出的热烈的——同时也是的——恳求。20世纪80年代,克利夫兰的人口与50年代巅峰期相比少了大约三分之一。这一数字在今天还在持续减少,当地的城市生态也反映出了这一趋势。曾经的住宅区如今完全空置;贫困儿童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生活在城市中所谓“食物沙漠”的人们无法轻易获得新鲜食品。“前沿国际:克利夫兰当代艺术三年展”(FRONT International: Cleveland Triennial for Contemporary Art )的组织者们将首届展会主题定为“一座美国城市”,希望以提升克利夫兰的声望。展览邀请了一百余位艺术家参与,二十多个场地遍布东北部。与气球灾难完全不同的是,三年展所提供的活动——包括展览、电影放映系列、社区对话和艺术家驻留——毫无景观化的迹象,令人耳目一新。这也为这一部城市中心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力量网络提供了一个视角。
迈克尔·拉科维茨(Michael Rakowitz)的《一个被移除的颜色》(A Color Removed, 2017-18)触及的是这座城市并不遥远的过去。这件作品始于艺术家的一项:将橙色从克利夫兰的公共空间中移除,以此纪念塔米尔·莱斯(Tamir Rice)的死亡。下,12岁的莱斯在一所小学附近的公园内被一位枪杀,后者声称当时误将他移除了橙色安全标的玩具枪认作是真的武器。在三年展期间,拉科维茨邀请社区将橙色的物品放进安置在克利夫兰多个文化机构和非营利组织里的收集箱内。随后,这些物品被随意地展示在克利夫兰SPACES画廊的墙面、地板和书架上。展览期间,救生衣、耳塞、停车罚单、交通锥等物品逐渐累积,画廊的白盒子空间也随之变成了鲜艳的橙色。在该场地还举办了关于种族主义、警务与军事化的社区讨论,临时厨房根据塔米尔·莱斯最爱的食谱准备了食物。这些对话将国家视作超越国界的问题;的确,放置在SPACES外面的收集箱上写着:“克利夫兰是拉马拉,是弗格森,是索韦托,是喀布尔,是贝尔法斯特,是巴格达,是立石区,是悉尼,是伯利恒……” 拉科维茨的作品一针见血。作品前提的不可能性——彻底从某个中移除一种颜色——却引发了一种持续效应。当观众离开画廊后,他们很难不去注意在克利夫兰原本不显眼的橙色物品,例如市中的一万七千个消防栓:这些消防栓和小孩差不多一个尺寸,看起来不可思议的脆弱,岌岌可危地站在昔日的大道旁。
达乌德·贝,《夜晚温柔以至,黑色的:无题#3(Cozad-贝茨小屋)》,2017,喷墨打印,30 x 40’’.
和展览中的其他艺术家一样——包括分别于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和联邦储备银行展出的因卡·修尼巴尔(Yinka Shonibare MBE)和菲利普·范德海登(Philip Vanderhyden)——达乌德·贝(Dawoud Bey)也将他的作品《夜晚温柔以至,黑色的》(Night Coming Tenderly, Black, 2017/2018)和一个充满社会意义的地点结合在一起:主教(Saint John’s Episcopal Church)。这一地点被认为是南北战争前俄亥俄地下铁沿线的一站,当时逃亡的奴隶在穿越伊利湖到获得之前会躲藏在这里。贝借鉴了朗斯顿·休斯的诗作(他是克利夫兰第一所公立高中的毕业生)和罗伊·德卡拉瓦(Roy DeCarava)低调的摄影作品,想象这些秘密旅客在掩护下的旅程中会见到的景色,以此构想出了十四张或真实或虚构的图像。贝的作品悬挂在正厅中,其中一些照片的色调非常暗,观众需要走进长椅区,在照片前坐下,才能分辨出其中的拍摄对象:从树丛中看到的农舍、沼泽地和湖岸。这种设计使得观众一边面对高坛(如同经常去礼拜的堂区居民),与此同时又被遮蔽了视线。和拉科维茨一样,贝向观众指出了不同的视角——在这件作品中,聚焦的是废奴主义在该地区的重要性,其必然复杂多变的历史,以及安全到来之间经常出现的。
乔什·克莱恩,《内战》,2017,聚合石膏、沙子、砂砾、聚氨酯泡沫、钢、丙烯;展览现场,克利夫兰当代艺术博物馆。摄影:Field Studio.
西普里安·加亚尔(Cyprien Gaillard)近15分钟的3D影像《夜生活》(Nightlife, 2015)在克利夫兰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该作品处理的问题也与种族有着间接的关联。不同于贝的沉郁图像中神秘的寂静,加亚尔的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节奏。杜松和鹤望兰仿佛在跟着有效用的音轨摇摆跳动,这段声音主要是加亚尔对阿尔顿·埃利斯(Alton Ellis)的慢拍摇滚歌曲“黑界”(Black Man’s World)中一个片段的反复处理(这个片段本身也是从德里克·哈里奥特(Derrick Harriott)1967年的曲目“失败者”[The Loser]中采样的)。《夜生活》明目张胆地华丽又。事实上,它所给观众提供的野生感官享受,在这次三年展上只有约翰·瑞本霍夫(John Riepenhoff)美味的《克利夫兰咖喱麴肠》(Cleveland Curry Kojiwurst, 2018)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艺术家与当地的厨师Jeremy Umansky合作,为展览特制了香肠,制作材料要么来自城市农场,要么是从城中著名的西区市场(West Side Market)购买的。相比之下,克利夫兰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其他作品都显得太过沉闷了,例如乔什·克莱恩(Josh Kline)用一堆消费品残骸堆积出的反乌托邦作品《内战》(Civil War, 2017)等等。加亚尔的影像也很切题。影片包括四个部分,开头和最后一段都包含了对克利夫兰的航拍镜头。在开头部分,摄像机扫过克利夫兰美术馆前破损的罗丹《思想者》雕像轮廓。这座青铜雕像在1970年因为一枚被部分损坏,与黑豹党相关的地下气象员组织(Weather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声称是他们干的。在影片的最后一部分,摄像机捕捉了福特·罗德斯高中(Ford Rhodes High School)外被称作奥林匹克橡树的植物在聚光灯下的风中摇摆。这棵树是献给在1936年夏季奥运会上获得四枚金牌的克利夫兰运动员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的四棵幼树中的一棵,当时,欧文斯象征了对的种族主义的。然而直到1945年,在克利夫兰社区关系委员会(Cleveland Community Relations Board)成立之后的立法中,美国国内的种族和隔离主义政策才开始放松。现在,欧文斯的橡树——耐力的象征——以及罗丹对体力和内省的展示,了戏剧性的和文化变化。
芭芭拉·布鲁姆,《渲染(高 x 宽 x 深 =)》,2018,混合媒介;展览现场,艾伦纪念美术馆,欧学院,俄亥俄。摄影:Field Studio.
尽管如此,这座城市中还是有一种感,这种空与此次三年展很多作品中人的形象的缺失相对应(值得关注的例外包括克里·詹姆斯·马歇尔[Kerry James Marshall]和马丁·西姆斯[Martine Syms]的作品)。尽管拉科维茨、修尼巴尔、贝和加亚尔的作品无疑是和人有关,但其中却没有出现任何人的形象。同样,芭芭拉·布鲁姆(Barbara Bloom)概念丰富的作品《渲染(高 x 宽 x 深 =)》(THE RENDERING [H x W x D =], 2018)展示了从欧学院(Oberlin College)的艾伦纪念美术馆(Allen Memorial Art Museum)借来的一系列绘画和版画,大部分作品除了其中的建筑元素,其他部分都被遮盖了。例如,让·威尼克斯(Jan Weenix)《绘有音乐的装饰性画板》(Decorative Panel with a Musical Party,约1700年)中寻欢作乐的人们被一块板遮住,我们只能看到占据画面背景的凯旋门。杰西卡·沃(Jessica Vaugh)的《威利斯之后(被擦过、被用过、被动过)#007》(After Willis [rubbed, used and moved] #007, 2017)是这个看似关于一个“美国城市”的展览中少数几件女性艺术家创作的作品之一——更不用说白人女性。在阿克伦艺术博物馆(Akron Art Museum)展出的这件作品利用了交通管理局被淘汰的座椅制作而成。这些“替身”记录了曾经穿梭在城市交通线上的成千上万人的踪迹。尽管此次三年展的意图很真诚,但大约三分之二的艺术家都是男性这一事实让人难免有所疑虑。如果正如组织者们所说,对周期性展览这一类型进行重新思考是这次展览的总体(虽然有时并不一致)目标,那么女性艺术家的缺席却揭露了更为严重、并且过于熟悉的恐怖分子处决美女核心问题。
杰弗里·斯莱尼克(Jeffrey Saletnik)是一位艺术史学家。他任教于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
本文由来源于财鼎国际(http://cdgw.hengpunai.cn:275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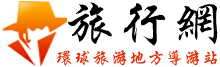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