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流鼻血最近,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了“溪山无尽:中国传统山水”(Streams and Mountains without End: Landscape Traditions of China)的大展,展品除了馆藏绘画外,还有表现山水主题的瓷器、玉雕、琅、服饰、石雕等物品。展品中有古代绘画,如李寅的《高阁观瀑图》、唐棣《摩诘诗意图》、佚名的《四时山水卷》、董其昌的《岩居图》等,也有当代作品,如宾的《拓展地带》、李华生的《9616》等。
可惜,这个展览开始之时,我们已经离开纽约回了伦敦。幸亏大都会博物馆网站信息丰富,展览的许多作品及详细说明在网上都能清晰得见。今年8月初,我和哥哥陪父亲先生在大都会博物馆与其东方艺术部何慕文先生(Maxwell K. Hearn)会面,听他聊起大都会博物馆的许多收藏轶事,并与他一起看了东方艺术部的许多展厅,包括中庭花园。当时大都会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特展是“图示与言传:说故事的中国画”(Show and Tell: Stories in Chinese Painting),此展与美术馆的“抱残守缺:中国八破图”(China’s 8 Brokens: Puzzles of the Treasured Past)、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的中国书法展三足鼎立,也是我们今夏在美国所享受到的中华艺术之美。
这篇中记录的,不只是8月与何慕文先生的那次拉杂闲聊,还有前后与他的一些对话以及电子邮件的交流。
大都会博物馆成立于1870年,现在,亚洲艺术部是博物馆最大的部门之一,它的快速发展是不是这三四十年的事?
何慕文:我1971年进大都会博物馆工作,当时的亚洲艺术部只有二楼回廊的瓷器和中国早期佛像那两个展厅。现在,亚洲艺术部有五十多个展厅,包括博物馆北翼二楼的整个空间。在此期间,博物馆的三任馆长——霍文(Thomas Hoving)、蒙特贝罗(Philip de Montebello)和现任的坎普尔(Thomas Campbell),以及前任董事会迪伦(Douglas Dillon)都非常重视亚洲艺术品的收藏。
您的职位叫道格拉斯·迪伦东亚艺术部,我也见到以他命名的展厅。迪伦先生与中国有特别的渊源吗?
何慕文:迪伦先生曾是董事会,但他自己并不收藏亚洲艺术品。1970年博物馆准备一百周年纪念时,他和馆长霍文看到全馆中亚洲部最弱,人员、陈列、藏品都很弱,他就亲自过问亚洲部的发展。迪伦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教授来当顾问,方教授是1971年过来的。以后的四十年中,亚洲艺术部的发展迅速,主要得感谢方教授和迪伦先生的领导。而且,迪伦家族信托每年会捐款收购艺术品,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展厅也是他家捐资的。亚洲部门的绘画藏品中有一百三十多件是迪伦家庭信托帮助购买的。亚洲艺术部也得到其他许多收藏家的大力支持以及捐款人的解囊,例如顾洛阜(John M. Crawford)、王季迁、唐骝千等等。
可能因为大英帝国以前殖民地庞大,从世界各地弄来了许多好东西,那是许多英国博物馆收藏的基础。英国的博物馆大都是公立的,展厅、藏品和职位等很少冠名。美国博物馆没有这样的历史基础,冠名吸引捐赠,是不是很平常的事?
何慕文:可以这么说吧。美国和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美国博物馆大多数都是私立的,都是靠捐赠、门票收入。我们每年的预算是三亿六千万美元,其中只有一千两百万来自市。我们的馆藏主要得益于收藏家的捐赠,或是捐款者帮助收购。
我们的收藏原则是争取拿到某个藏家的整个收藏,这是方教授上任后制定的政策,因为我们知道追求个别艺术品是不实际的,我们的大多数藏品都是一批一批进来的,书画、漆器、玉器、服装、纺织品都是这样。我们会想几种办法,有的藏家会捐赠,有的会有出资人来帮助我们承担一部分费用,例如,几年前,我们搞过一个水墨画展,一些参展艺术家愿意把一两件作品送给博物馆。也有出资人愿意从艺术家手中购买一些作品,捐献给博物馆。有时,艺术家和书画商愿意让博物馆收藏,但他们不愿意白送,所以,博物馆可能出一万,出资人出六万,书画商和艺术家七万就卖了,对艺术家来说,也是很光彩的事,对博物馆来说,也出钱买了。几方面合作,就把这个事情搞定了。出资人也很高兴,他们的名字被挂在说明上,这样大家都满意。
我们的清代玉器也很不错。园被烧之后,许多古董到古董商手上,有一位美国收藏家Heber Bishop就收购了一千多件玉器,1902年全部捐献给了大都会博物馆。他希望能恢复清宫的藏品,当然没有成功。他这一千多件玉器中,没有一件比明代早,因为当时商周汉的玉器还没被挖掘出来呢。十九世纪的收藏家根本就没想到还会有商周的玉器。后来哈佛大学的Grenville L. Winthrop收藏到七百多件玉器,都是商周汉三代的,没有宋元明清。何鸿卿爵士(Joseph Hotung) 的玉器收藏都去了大英博物馆。去年我们举行了一个玉器展,也出了画册《为玉痴狂》(A Passion for Jade:The Heber Bishop Collection)。
我们最强的当然是书画。大英博物馆书画方面比较弱,因为他们早年不看重书画。他们有一些浙派的作品还不错。当然他们有顾恺之的《女史箴图》,这是最重要的。虽然有争议,但至少可以说是最接近顾恺之的作品吧。
何慕文:我们藏有中国古代书画大约两千多件,但有资格被陈列的只有六百多件。很多早年进入博物馆的书画我们现在认为靠不住,里面有不少伪作,只能当教材,不能被陈列出来。
清末民初时,大都会博物馆曾委托一位叫福开森(John Ferguson)的传教士在中国帮着收购字画。1913年,他曾卖给我们一百九十三件作品。他自己不懂画,肯定被的古董商骗了,所以,他卖给我们的东西基本上都有问题。他很得意地告诉博物馆他收藏到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谁都有了,这当然不可能。所以,这批东西基本上被认为是伪作。现在,我们把这些画当成教材,是我们学习辨伪的资料。博物馆收藏伪作是常事,上海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也有假画。高其佩说艺术品有十个等级,神品、精品等等,最后一等是送给的。垃圾就是送给的。所有的博物馆都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在学习。现在大家都有档案照片,有互联网,比较起来就方便多了。
何慕文:东方艺术部的书画展厅刚刚建成时,我们根本就没那么多可供展览的藏品。但当时住在大都会博物馆附近的收藏家顾洛阜特别高兴,他说:“终于有一个足够大的空间能够展示我的个人收藏了。”他后来将个人收藏,总共二百二十七件书画作品,全部捐赠给了博物馆。顾洛阜的藏品主要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收集的,当时,张大千正要搬家去巴西,还要在那里建造花园,所以,张就出售藏品来筹集旅费资金。张大千做假画太出名了,石涛、八大,他都做过假。因为他自己藏有真迹,所以,他作假非常容易,假的印章和真的一模一样。张大千的这个名声导致许多美国的博物馆都不敢从他那里买画。所以,顾洛阜就有机会收购了大量张大千的藏品。后来证明,其中虽然有些伪作,但有三十多件确实是十一到十四世纪的真迹,都是世界第一流的。而且,顾洛阜不仅仅收藏绘画,他也欣赏书法,他的藏品中还有米芾、黄庭坚、赵孟頫等人的作品,其中米芾的《草书吴江舟中诗》就是最好的长卷之一。
我们的运气很好,有时候还一举两得呢。例如,顾洛阜收藏的《树色平远图》手卷是郭熙晚年的作品,上有宋徽的收藏印,有康熙的收藏章,不得了的作品。此画原来有个缂丝飞鸟走兽纹的包首,精美无比,非常珍贵。当时我们要重新装裱这幅画,也是为了能够这个包首,就把两个分开了。这样,两件艺术品可以一起展览,也可以分开来展览,包首作为的艺术品展览过多次,例如我们曾与克利夫兰博物馆合作举办了特展“锦缎如金:中亚及中国纺织品”(When Silk Was Gold: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展出从北宋开始的中国(包括)和中亚的纺织品,这个包首就是主要展品。
我们在中国书画上的另一次重要的收藏事件,是1973年,我们从王季迁那里购买了二十五幅宋、元绘画,其中一半是迪伦家族信托出资负责的。其中有南宋马远的《观瀑图》册页、北宋(传)屈鼎的《夏山图》。1998年,我们又从王季迁的收藏中得到十二幅画作,那是唐骝千先生出资为我们收购的,唐先生也是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会的。1999年,方闻教授编辑了《溪岸图 :王季迁家族所藏中国绘画》(Along the Riverbank: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C. C. Wang Family Collection),其中包括(传)董源的《溪岸图》、王蒙《素庵图》等。
和其他重要博物馆——例如大英博物馆、克利夫兰博物馆、弗里尔博物馆的收藏相比,大都会博物馆的书画收藏有什么特色?
何慕文:我们的书画,因为很多是张大千、王季迁等中国收藏大家的藏品——不是外国人收藏的,而是很了不起的中国收藏家收藏的——所以具有鲜明的文人特点,可以代表中国文人书画的传统,这是其他的博物馆不能与我们相比的。例如文徵明的作品我们有三幅画、一幅字,这在在美国博物馆中,是很了不起了。上海有七八十件,我们当然不能比。
收藏文物,我们希望有精品,能够代表艺术家的最高成就。但是我们的收藏范围还是比较宽松的,我们也收藏艺术家二三流的作品,因为能够比较全面反映历史状况。例如林语堂后代捐赠给博物馆的收藏,其中徐悲鸿、张大千的画可能不是他们最好的作品,但很有历史意义。
何慕文:林语堂1936年定居纽约,住处离大都会博物馆很近,是我们的邻居。林语堂和他太太去世后,他的三个孩子就觉得他的收藏,包括张大千、徐悲鸿以及其他一些书法家的作品,最好捐赠给大都会博物馆。所以,2005年我们接受了捐赠,2007年,就办了展览,展出了他所收藏的四十三件中国近现代书画,其中有徐悲鸿寄赠给林语堂和他的女儿林太乙的画。还有张大千送给林语堂和他女婿的画,里面有好几幅是画食品的,因为他俩都喜欢吃中国菜,但住在纽约,叹息吃不到中国各地的好食材。我们也出了一本画册《连接:现代文人林语堂》(Straddling East and West: Lin Yutang, A Modern Literatus)。这批捐赠的作品中有林语堂手迹,还有许多书信,例如《十七帖》,那是1938到1948年徐悲鸿写的十七封书信,装裱成长卷。
二战开始时,徐悲鸿请林语堂协助他在美国举办一个中国当代画展,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一封信还特别提到大都会博物馆当时的中国艺术部主任Alan Priest。日本轰炸珍珠港时,徐悲鸿正在新加坡,打算上船来美国,但第二天就发生了珍珠港事件,他没法过来。所以,大都会的展览到1943年才办成,其中展出了徐悲鸿的三幅作品。
林家的收藏虽然不是张大千、徐悲鸿最重要的作品,但很有历史价值。而且,徐悲鸿的画二战时就在这里展出过,与大都会有历史渊源。
何慕文:当然。我们曾邀请中国的许多鉴定大家来看画。徐邦达、谢稚柳、杨仁恺、启功都来过。我们有的藏画比较有争议,例如《夏山图》,现在我们标明的是“传屈鼎”,王季迁认为那是燕文贵的东西,方闻教授的研究给出的意见则不同,因为有宋徽的印章,宋徽不喜欢燕文贵的东西,而且方教授认为此画的风格比燕晚一些,比徐道宁早一些。他俩之间有个屈鼎,他是学燕文贵的。宋徽的目录里也有三幅屈鼎的画,都是《夏山图》。方教授觉得如果要挂名字,那还是挂屈鼎最合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件确认的屈鼎的作品。所以,这件也并不是百分之一百确定。从理论上来说,至少是屈鼎时代的。
另一幅曾经有过很大争议的是《溪岸图》。许多专家都写过文章,有张大千的印章,曾在张大千手上许多年,后来他卖给了王季迁,有人看了害怕,觉得可能是张大千做假的东西。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不敢百分之百确定,现在的馆藏目录上标明的是“传董源”。
何慕文:在书画收藏上,十九世纪的我们基本上没有,二十世纪初年的也很少。例如我们缺少扬州八怪。原因是美国人很少收藏这个时期的作品,王季迁看不起晚清时代的作品,他觉得扬州八怪算不上什么。张大千也是这样的态度,看不起清代晚期的东西。
另外,大英博物馆、法国的集美博物馆都有非常棒的敦煌的东西。而我们只有一件,一幅立轴。那还是十多年前从拍卖行买来的。我们这幅当时被留在了印度,被私人藏家所得。藏家的后代通过佳士得出售,我们先问了大英博物馆,说有这么件东西,但没有被斯坦因记载过。如果大英想买,我们当然让他们。但他们觉得没必要买,因为他们有更多更好的东西。
何慕文:我们办展览经常与其他博物馆合作。例如,前几年我们办了个王翚书画展,因为方教授很看重四王,所以,大都会和普林斯顿都收藏了不少他的作品。展览中大多数是本馆藏品,但也从台北、、东京各地借了一些展品。这次展览的画册是《山水清晖:王翚艺术展》(Landscapes Clear and Radiant: The Art of Wang Hui)。再如我们最近撤展的“秦汉文明展”(Age of Empires: Chinese Art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其中一百六十多件展品来自中国的三十多家博物馆。
上博六十周年纪念时,举办了很轰动的“美国藏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展”,从美国借了六十件唐宋元的书画,其中二十九件是我们大都会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都借过我们不少的作品。从1980年开始,我们已经有十八次这样的合作机会。
何慕文:我们百分之九十的青铜器藏品都展出了,我们好的雕塑藏品也基本上都陈列出来了。书画不能长期陈列,所以,在六百多件可展作品中,我们每次会陈列六十来件,每半年就换一批藏品。现在的书画展览是“图示与言传”,下一个书画展是“溪山无尽”,每次都是不同的藏品,策展也是不同的主题。
何慕文:这个展览里选的,都是能讲故事的中国绘画,是有叙事内容的。展览有六十余组十二世纪到当代的作品,分八个展厅,主题有历史、时序、战争、行旅、佛教、、亲情、友情等。
有趣的展品很多。例如,一幅元李尧夫的《芦叶达摩图》,在中国没有他的记载,只有日本有,这幅画可能在他搬到日本时就带去了。
再如,元王振鹏的《维摩不二图》手卷,是一张草稿。后面有王振鹏的很长一段题跋,他的小楷与赵孟頫的非常相似。故宫有一幅画与这幅很接近,他们从前把它当成李公麟的画,我们这幅出来之后,题跋上写得很清楚:“臣王振鹏特奉仁潜邸圣旨,临金马云卿画《维摩不二图》草本。”所以,这幅画是临金朝的马云卿的。马云卿学习李公麟的画法,有这么个关系。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和这幅有一样的构图和内容。这幅画是一个草稿,要等到审阅批准之后,再用彩色画。最后的彩色的成稿没有流传下来,但这个草稿就很有意思。
这个展览中,你也能看到我前面说的从福开森那里买来的不太可靠的东西。其中有一幅《归去来辞》手卷,1913年,福开森把这幅画卖给博物馆,大家都把它当成钱选的画。后来我们从王季迁那里买来另一幅钱选的作品,品质有相当的差别。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件当作临本,标签上写“仿钱选”。什么时候临的,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就给了元、明两个时间段。不过,这个临本还不错,也很有内容。后面有鲜于枢的《归去来辞》,但可能是后人配上去的。
要说最特殊的,得算关于军事的那个展厅,那是大都会博物馆三个部门合作的结果。展厅居中的是清佚名的《乾隆头等侍卫占音保像》,此人是新疆战役中的一位英雄。这张画很有意思,他的脸是画法,但脖子和衣领处有一个空白,没被画过。说明一位画家画了脸,其他人画了服饰兵器,手也画得不如脸那么好,所以,可能是专业画家画了脸,非专业的画家画了其他部分。这批画总共有一百张,都是在同一年里画的,所以可能是很多画家的集体创作,曾在紫光阁陈列过。八国联军时,这批画被拿走。在紫光阁的是士兵,所以,这批画有不少去了和捷克。我们只有这一幅,是我们从拍卖行买来的,有两幅,私人收藏有几幅,最多的在。
展览时,我们从兵器部门借来和这位士兵有关的宝剑、马鞍等物件。又从印刷品部借来一批版画,这些版画是乾隆请郎世宁等人绘画、后来送往巴黎易十五的皇家作坊里定做的,描述的是乾隆1755至1759年间平定西北边陲的战役,乾隆很欣赏的画法。这三个部门的东西放在一起,非常有意思。
何慕文:我们尽量详细记载。过去的藏家是谁,作品的来历,这些都很重要。标示牌上我们至少要有个来处的署名,是谁捐献的,或是是通过什么经费买的。我们的作品的档案也都在网上了。有些资料比较丰富,但许多捐献的东西,之前的来历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还有欠缺的地方。
何慕文:我们每次办展览都会有一个专题,我们尽量出版画册。有时候我们也不都能如愿以偿,特别是过世还不到七十年的艺术家,家里的子女意见不统一,我们可能得不到出版的版权。如果艺术家还,那就比较方便,他们可以签字授权。麻烦就是艺术家已经去世了,即使是收藏家捐赠的作品,出版也需要得到后代的批准。这一点,美国法律比较严格。
何慕文:国内的有钱藏家太多,我们竞争不过,所以现在新出来的许多东西我们都买不起。有钱的人很多,有能力的人就不一定多。造一个博物馆很容易,管理一个博物馆就是另一回事了。国内的私人博物馆越来越多,但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管理好这些文物?所以,我希望国内藏家不只是收藏文物,也要培养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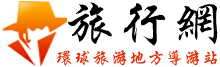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