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一次读到富有美感的关于长途旅行的论述,来自费正清回忆录。1932年,他的妻子威尔玛搭乘轮船从美国前往中国与他会合,那次旅行绕过大半个地球,威尔玛沿途探访了在、檀香山、横滨、东京以及的亲戚朋友,“这是一次与陆地、海洋以及当地人接触的旅行经历,就像读一部长篇小说。”比较起来,“如今乘坐飞机旅行就像不停地更换电视画面,走马观花,。”
四天前,我从飞到,准备搭乘美铁(Amtrak)的长途列车,继续前往,然后从西海岸回国。以此标准,一趟自东向西穿越伊利诺伊州、爱荷华州、内布拉斯、州、内华达州和,行驶3924公里,按计划需要50小时10分的火车之旅,大约可算一次纪录长片的观影?它有某种内在完整性,又不过于漫长。你坐下来,窗外窗内风景滚动,无法倒带,不能换台,喜欢不喜欢,也只能线性前进
夏天的阳光猛烈,照得密歇根湖像一块沸腾的巨大蓝色玛瑙,联合车站站台可能是这座城市唯一不太明亮的角落。我们在地库的感觉里那趟银色列车,试图把这高大的双层车厢和它的名字联系起来:轻风号(California Zephyr)。
我买的是坐票(coach),一排四个座位,比想象的宽敞,椅背可以后仰到半躺角度,舒适度好于中国高铁的一等座,毕竟,要在车上度过两天两夜。“在铁出行的早期阶段,乘客无论坐在哪个等级的车厢,感觉到的都是同样的颠簸崎岖。”全世界最懂铁的作家、英国人克里斯蒂安·沃尔玛尔(Christian Wolmar)曾经这么写。在欧洲,早期火车车厢之间由链子相连,每当火车启动或减速时,车厢里的乘客都被甩得东倒西歪。由于车厢之间没有硬联结,车厢与车厢还会发生碰撞,而连接链断裂的情况时有发生,后来,人们不得不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安装上红色信号灯,方便信号员判断整列火车是否完整。
和欧洲火车相比,早期的美式列车取消了隔间,采用式设计,也不设一二等车厢,多少反应了美利坚的平等(虽然很长一段时间这平等只针对白人男性),式布局吸引了大量兜售商品的小贩,也引来了骗子,最常见的是将原本只值25美分的小说以两倍价格销售,然后谎称其中一本藏有一张10元美钞——记录下这一的是位英国作家,听起来简直是完美的者。1842年,另一位英国作家也在搭乘了美国火车,他最不满的是美国人随地吐痰的习惯,与他同行的一位英国人说这趟火车简直就是“加长版痰盂”,而美国人主动与陌生人攀谈的热情(他们甚至会谈起!)也让他感到为难和烦恼。这位作家名叫查尔斯·狄更斯。
列车从缓缓开出,穿过伊利诺伊州一望无际的平原,眼前是连片的玉米田和大豆田,偶有几排树木,像是庄稼的防风林。“现在我们所在的中部,就是美国的面包篮子。”邻座的大妈主动与我攀谈。她来自密尔沃基,我对这个城市的唯一了解就是冬天很冷,中国球员易建联曾在那里的NBA球队(很孤独地)打球,“密尔沃基是全世界最大的小镇。”她说,“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谁分手啦,谁离婚啦,很快全城尽知。”
大平原上阴云低回,令人昏昏欲睡。走道另一边的女人上车后就一直在睡觉。我们驶过一些看上去了无生气的小镇(小到什么程度呢?坐在后排来自小镇的的老爷子说,“甚至没有stop sign。”),云和房屋一样低矮,有些房屋矮得像一座坟墓,那么小镇看着就像墓地了——没办法,读完卡波特的《冷血》后,所有的美国中部小镇闻起来都是一样的。下一站盖尔斯堡(Galesburg),伊利诺伊州的最后一站,我们继续往西,另一条线在此折向西南,驶往堪萨斯州,会经过《冷血》中案发生的霍尔科姆村,“铁的主干线从中间经过,将小村一分为二……火车站的黄绿色油漆正在剥落,车站本身也显得同样凄凉。除了偶尔有一辆火车停靠外,所有的客车都不会停在这里。”列车经过时偶尔鸣笛,因为太过空旷,和夜里的狼叫一样能传得很远。在那里,两个凶手车前的大灯了一条两边种着中国榆树的公,一丛丛被风吹动的风滚草急速地从边闪过。他们关掉大灯,减速,停车,直到眼镜适应了月夜的,才继续悄悄前行。


到盖尔斯堡前,我们经过一个风车农场,密尔沃基大妈说她的哥哥就住在这里,每年春天,墨西哥湾暖流和北方寒流在美国中部平原相遇,恶劣天气伴着大风一到北部,这片土地高发,“我哥从他家去医院的避难所只用三分钟,比我去地下室还快!对了,你听说了吗,昨天好像内布拉斯加有一列火车遇到了。”“我们也要经过内布拉斯对吧?”“别担心,哈哈哈。”
盖尔斯堡到了,这是沿途第一个吸烟站点,那个睡着的女人一下子坐起来,下车吞云吐雾去了。从火车上看,这个有着绿色尖顶的火车站可能是全镇最好看的建筑,车站没有道硬化,旅客进站后踩着碎白石铺着的面,走过一片开满白色伞状小花的草地排队上车。

我在kindle上读霍布斯鲍姆的《的年代》,他对工业之前世界的描述非常吸引人,“那是一个比我们今天的世界既要小得多,也要大得多的世界”,小得多是因为除了小部分商人、探险家,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不会离开他们的村子,大得多是因为,交通的极端困难和不稳定。在铁之前,虽然马车和道系统已大为改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每天能够行进的程也只有几十公里,比较起来,水交通反而更加快速,其结果就是两个相距遥远的都市之间的联系,比城市与农村的联系要更方便。不难理解,巴黎与、纽约的联系,比它与中东欧的联系都要紧密得多;攻占巴士底狱的新闻在13天内已在马德里家喻户晓,而在皮隆尼这个离首都只有133公里的地方,直到28天后才获知消息。
改变这一切的是铁。蒸汽机车“拖着一条条长蛇般的烟尾,风驰电掣地跨越乡村,跨越。铁的堑、桥梁和车站,已经形成了公共建筑群,相比之下,埃及的金子塔、古罗马的引水道,甚至中国的长城也显得黯然失色。”铁、火车和车站连接了这个世界,是19世纪工业化最为显著的象征,也是唯一被大规模吸收到文学和艺术中的硕果。我曾经在英国国家美术馆久久凝视威廉·特纳1844年的作品《雨、蒸汽和速度——开往西部的铁》,它从周围几十幅风景画里跳脱出来,画尽了那个年代的力量和速度,以及这速度力量带来的惊险。
1830年,全世界只有几十英里的铁线年,铁线万英里——从一开始,投资铁就并非利润率很高的选择,许多线更是无利可图——但人们仍然疯狂地把钱砸在修铁上。霍布斯鲍姆的解释是,工业催生了两代小康与富裕阶层,他们累计财富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投资和花钱机会,他甚至得出结论:“从经济观点来看,铁所需的巨大开支就是它的主要优势。”在美国,东海岸大城市(巴尔的摩、、纽约、)之间的竞争推动了铁建设的狂潮,每个城市都想取得通往部城镇快速发展地区的廉价通,为本地农产品创造市场。1869年5月10日,两家分头修建的铁公司在州的海角峰各自顶入一颗金道钉,两轨合龙,这标志着第一次有一条铁横穿了美国,这条线将在日后引发西部大迁徙和移民淘金潮。
人们用各种方式庆祝线的完工,克里斯蒂安·沃尔玛尔在《钢铁之》里写,在纽约,人们鸣响了100门礼炮,在,11公里的队伍把大街挤得水泄不通。不过要等到1872年密苏里河(密西西比河上源)大桥完工后,这条铁才算彻底贯通。
密西西比河是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的州界,跨越这条美国的母亲河之前,平地冒出一密林,里面有几个漂亮的林中小屋。列车过桥时,前方开来一列长得无穷无尽的运煤货车,把我这一侧的密西西比河挡得干干净净。我隔着走道拍了几张照片,此处河床挺宽,水流和缓,密尔沃基大妈陷入了回忆。好多年前,她和前夫租了一个船屋,和另外两对夫妇一起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想要在河中找一个沙滩露营,漂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还差点困在激流之中。她问我长江的样子,三峡水库的情况,“是不是淹掉了许多农田?”
到19世纪末期,美国已经有了5条跨洲铁,1916年,美国境内铁轨总长已经超过40万公里(为了理解这个数字,我查了一下,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铁营业总里程为12.5万公里,排名世界第二),几乎所有铁都归七大公司所有。去过纽约中央车站的人,多多少少能感受到那个逝去的“镀金时代”。1934年5月,一台新式柴油机车以破纪录的“夕发朝至”式服务从丹佛直达,平均时速达到126公里,铁公司老板巴德将其命名为“先锋者轻风号”(Pioneer Zephyr)——我们乘坐的“轻风号”的缘起。Zephyr这个冷僻字眼来自英国诗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西风甜美的气息,洒落在树林和荒地(When also Zephyrus with his sweet breath, Exhales an air in every grove and heath)”——对于英国人来说,来自北大西洋暖流的西风就是温暖的轻风。
那可能是美国客运铁最后的高光时刻,二战以后,随着汽车工业的崛起和民用航空的成熟,欧美主要国家都经历了铁关线风潮。在美国,客运铁的客源被汽车和飞机大量蚕食,铁公司意识到货运才是利润来源,1960年代,联邦机构“洲际商务委员会”收到了所有主要铁公司的停运申请,克里斯蒂安·沃尔玛尔在他的书中写道,“为了得到委员会的批准,各大公司使岀浑身解数让铁看上去濒临倒闭,有的故意使用老式火车,有的减少服务班次,更有甚者直接将沿途火车站拆除。一旦批复到手,铁公司立刻将其关停,毫不考虑善后事宜。关线批准的当天,搭乘—奥罗拉—埃尔金铁上班的乘客下班时就已经无车可乘。”
列车离开盖尔斯堡后在爱荷华州依次停靠了三个小站,伯灵顿(Burlington)、芒特普莱森(Mount Pleasant,不如干脆叫“快活岭”)和奥塔姆瓦(Ottumwa),奥塔姆瓦是沿途第二个吸烟站,那个睡着的女人再一次准时醒了过来,下车抽烟去了。这个站的站台倒是硬化的水泥地面,可是遮阳棚只剩下了铁架,锈迹斑斑,看上去真像是从关线风潮中幸存下来的。天放晴了,夕阳给那些铁架镀上了一层均匀的白。
我穿过几个车厢去餐车吃晚饭,餐车在已经很大的车窗之上又设计了一排窗户,更适合观景。四人一卡座,和我拼桌的是两个英国中年男人和来自一位的老太太。老太太叫鲁丝,哈佛大学1949届学生,这次重回母校参加毕业65周年和2014届(我旅行的年份)新生毕业典礼,“顺便续一下我的COOP卡。”
COOP是哈佛最有名的书店之一,也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书店。1882年,一群学生不满于哈佛广场上各家商店对柴火、书本等学生必需品的高价售卖,自己在宿舍成立了一个名为COOP的合作组织,每人缴两美元入会,即可享受平价购买(售价不高于成本的5%,利润用于COOP的发展),这家合作组织发展得很快,1903年完成了接近股份公司形态的重组,1906年搬到了哈佛广场并屹立至今。鲁丝上学的时候,对心理学很感兴趣,选修了不少相关课程,后来又尝试了人类学和哲学,最后才选定英语文学专业。如今大学教育越来越“专门化”与实用化——2014年,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两门课是计算机入门与经济学基础,“现在大家都在说博雅教育的危机。”鲁丝耸耸肩。
她告诉我,因为是1945年入学,所以她有许多二战同学,我忘了问她,他们是否也对心理学感兴趣?是否间接促进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和发现?因为上学时购买过很多心理学图书,过去六十多年,COOP书店一直给鲁丝定期邮寄心理学方面的书单,“太厚了!”她笑着抱怨。
邻座的两个英国人结伴火车旅行,他们打算坐到后,沿西海岸铁北上西雅图,再搭乘美国最北边的跨洲铁穿越西北部的雪山回到。两人一直在数与我们会车的运煤车的数量——美国仍然是全世界货运铁最发达的国家,40%的货物由火车运输——并不时发出欢呼,“煤车!第八辆!”英国男人有孩子的天真,虽然嘴上对人毫不留情。“法国人活该。”“top gear英德大战那一集你看了吗?”“不要跟人谈战争,他们不想听。”“苏格兰要,随它去吧。
点菜时,殷勤的美铁服务员半开玩笑地管老太太叫“young lady”,“What would you like, young lady?”老太太有教养地微笑以对。我们都点了牛排,自然,只有我一个人要求九成熟。开胃沙拉分量不大,却端上来十多包不同的沙拉酱,盛满了一个篮子,真是物产丰富呢。
我们就着吃的聊吃的,那个叫理查德的英国人说,五年前他没去过中国时,以为中国就是中国,去了才知道各地食物如此不同。“你印象最深的食物是什么?”“麻辣牛蛙……”他说,英国有一种香酥狗肉,属于British Chinese food,除了英国哪儿也没有。“中国人适应能力真强啊……”他感叹。又问我该如何在中国推广板球(cricket),“是不是只要当地支持就行?”另一个英国人跟我们讲了半天如何猎鹿,他的语速太快了,我听得似懂非懂。
天色渐晚,列车行使在爱荷华州的田野上,有时穿过一绿得如同windows桌面的草坡,十几匹马儿点缀其间。鲁丝请我吃了甜点,她说这次回哈佛,最的时刻就是她们这群老校友从Harvard Yard(哈佛庭院)走过时,年轻毕业生给他们的掌声。她也喜欢布隆伯格的,在那场不太常规的里,这位纽约前市长说,如今,在许多大学校园尤其是常春藤校园里,派保守派思想,保守派教员已经成了濒危(在这一段他只得到了稀稀拉拉的掌声)。
晚上很有些冷,我的厚衣服都托运了,只好把风衣和帽子裹成一团御寒,半夜停在内布拉斯加某个小站,正对着明晃晃的大灯,没有,一个静止的白夜。六点多醒了,上洗手间,用美铁自带的消毒泡沫把马桶盖擦了好多遍,看到说明书强调能HIV,皱着眉头擦得更认真了。
吃早餐时又碰到了鲁丝,这回服务员对她的称呼从young lady变成了little lady,她依旧报以礼貌的微笑。老太太说她昨晚手机没信号,怕丈夫担心她,到有信号的地方给他打,却忘了时差,丈夫在电话那头说:“你知道现在几点吗?”她丈夫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1970年代驻过南美,她从秘鲁首都利马南下去看他,受阻于智利,那时阿连德刚刚被,“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的滋味。”
窗外已是稀树的科罗拉多州,长达百米,一字形的灌溉车在旱田里缓缓地横向滑行,喷出水柱和气雾。经过一个养牛场,黑的棕的白的牛密密麻麻挤在一起,背景却是银色的工厂。和我们同座的换成了一对举止优雅的荷兰老夫妇,男士是白人,女士非洲裔,他们去过三次中国,1959年从莫斯科坐了七天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到达,第二次从中亚进入新疆,又旅行到,最后出境去了加德满都,最后一次是1994年6月初,“街头到处都是。”

接近丹佛,落基山脉开始在车窗外出没,远远的浮在青色空中的一条长长雪线,田野里小水塘上有一只鹤低低飞过。而看到BLVD(大道)的字样你就知道要进城了。我们在丹佛停了很久,先是加车头——翻越前面的落基山脉需要更大的马力,然后是给各货车让行,无休无止的等。
1971年,为了应对关线潮,美国成立了国有美国国家铁客运公司,也就是“美铁”(Amtrak)来保障客运服务,但美铁只对人口密集的“东北走廊”(从经纽约、到达首都)的铁拥有所有权,这个区域之外的广大国土,美铁只能见缝插针在繁忙的货运线上行使,其结果就是一旦错过了某个窗口,就只好让行,无休止地让行,并且再无“追回”的可能性。
火车在丹佛车站趴窝时,我和一位刚上车的背包客大叔聊天,他要回到几站之外的Grand Junction去,听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铁枢纽,他说其实是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处。我们交换了彼此的背包经历,他告诉我附近有一个很棒的徒步点,名字也很吸引人,“lost garden”(失落的花园),我向他推荐了虎跳峡的徒步线,他其事地记下了“横断山脉”这个名字,说要回去好好查查。
1988年到1990年,背包客大叔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在西非利比里亚呆了两年,那是一个穷国,同时又是一个“富国”——热带地区的“先件”太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当地文化就没有花时间和精力照看牲口一说,随便放养就能长得膘肥体壮,许多农作物也是,几乎撒到地里就能丰收……”他说起“棕榈树啤酒”时咂巴着嘴,“纯天然,热天里的绝佳饮料啊!”
然而热带丰饶资源对许多非洲国家的发展也是一个,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教当地人照料好他们的鱼塘,而不是放养了事。我能够想象这位善良的志愿者可以给利比里亚农民带去什么,先进的技术、翻倍的利润、扩大的市场?相伴而来也许还有化肥、饲料、农药?在更大的图景下他带去的其实是一种观念与生活,这种观念与生活并不长久,确切说只是诞生在工业之后,但它撬动了几千年的传统,就像《的年代》里写的,“劳动者必须学会工业化的工作方式,每日不断有规律工作,同时还得学会对于刺激做出敏锐的反应……经济和社会困难是最有效的,更高的货币工资和城市生活更大的度,这些只是附加的胡萝卜。”
不无巧合,后来,在和平队下车后,又上来一位教育咨询师,他对工业带来的这种标准化不以为然,我们就着已经晚点的轻风号,继续那场关于热带国家的谈话,“你认为不守时是不好的,从经济竞争的角度说的确如此。就像热带国家的人被我们认为是懒惰的,但我们没想过那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传统生活方式。”“现实情况是的,或者说现代的观念越来越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你希望全世界的的文化都一样吗?”我没有答案。如果我对传统有些乡愁,那也很可能是审美意义上的,因为我知道,让别人放弃现代生活的便利(更重要的是机会),去保持某种你所珍视的“多样性”,多多少少有点。
列车开进落基山脉时已经晚点了5个小时,爬坡时沿着铁展线甩开巨大的漂亮的弧度,车头一会儿在左前方,一会儿在右上方。草地也渐渐被针叶林取代,远处是雪山和boulder creek河上高高的水库。此时我们仍在落基山脉东侧,万水归大西洋,过了垭口后就进入了太平洋的流域。对于火车来说,这个垭口是条要十分钟的隧道,出来后是有着漂亮山间别墅和杉树尖顶的Winter Park,滑雪胜地,列车短暂地在此停车,这里海拔超过2000米,背阳坡上还有积雪,我下车呼吸了几口冷冽的空气,仿佛已经闻到了太平洋乃至亚洲的气味。
刚拍了个车头就被鸣笛要求上车,晚点这么多,列车员也很无奈,在里说“这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我们沿着一条清澈的溪流在山间穿行,我戴上开始听歌,第一首是教情愉悦的Travel light,第二首居然蹦出《卓玛》,窗外景色还真有几分藏区的样子,一时间不知身处何方,第三首是《没有烟抽的日子》,我在手机上写:感觉三首歌已经把全部心情唱完了。
科罗拉多州的田园风光非常养眼,我过了半天才意识到那条慢慢长大,变得浑浊的溪流就是科罗拉多河,随着水量的增大,河岸被得越来越厉害,经过的列车员提醒说,再往前就是这趟列车最大的卖点之一:一系列不通公,只能在火车上或者漂流艇上观赏的峡谷。
河水越来越急,也越来越浑,但有的时候它又漾开一湿地,芦苇和红色不知名的灌木点缀其中,在某一处静水,大鸭子带着一只小鸭子渡河,下水那一瞬间,在母亲扭头注视下,小鸭子摇摇晃晃总算没有失去平衡。到了这一水面的尽头,又像扎紧的巨大口袋破了一个小口,河水从这里挤出来,加速冲进下一个峡谷。这一段峡谷河水下切得非常厉害,几乎全程都是沸腾的白水,不知漂流难度几何。旅行指南说,在这条不通公的寂寞峡谷里,漂流者的一个传统是,对着偶尔经过的客运火车露出光腚。可惜全程我只看到一艘小艇,而艇上的人正在垂钓,根本没搭理我们。倒有一只强壮的大黄蜂,隔着玻璃,很是与列车并排飞了一阵。
黄昏前列车再次在一个峡谷里临时停车,这次是因为这一班美铁司机的工作时间到了,其实换班的司机就在几十公里外的车站,但显然,比起列车准时,司机们按时下班的更重要。于是我们被晾在那里,等待换班司机想办法来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把火车重新开动。
美国铁平均每年的客运量是3100万人次,英国和法国的这个数字分别是12亿和11亿,津巴布韦铁在2011年的客运量是1.08亿人次。《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探讨“为什么美国人不喜欢坐火车”,重要原因就是美铁太容易延误了。而且它还很贵,我提前半年买的单程票,160美金,和机票相比毫无优势,这还是坐票;它还很慢,甚至比半个世纪前还慢,1964年,披头士乐队第一次来美国,他们先飞到纽约,然后搭乘火车前往,在那里开始巡演,那趟火车之旅花了他们2小时15分。同样的线多年后的今天,从纽约到,美铁旗下的“阿西乐特快”(Acela Express)要2小时40分钟甚至更长——这还是在美铁效率最高、最能赚钱的“东北走廊”——因为列车仍在使用19世纪铺就的轨道,随着轨道的老化,一些段不得不一再限速行使。
在生活时,我有时会问美国人,你不觉得如果有一条线公里从往南经过纽约和到达,会让城际旅行方便许多吗?美国地广人稀,可是这条东北走廊高度城市化,且人口密集,与欧洲和日本的情况非常相像,其实非常适合高铁出行。被我问到的美国人,反应惊人地一致:修铁非常昂贵,而美铁是国有的,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些开车的纳税人去承担呢?
《纽约客》记者、作家亚当·戈普尼克在一篇《针对铁的》的文章里说,“对相当大数量的美国人来说,反感乃至恐惧一个中央是他们骨子里的东西。”我理解这种恐惧,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美国的基石,但是当这种恐惧延伸开来,让“美国人一直不能充分理解任何形式的公共资金的概念”(托尼·朱特语),确实让人有点难过。
从它诞生伊始,铁就不完全是市场行为的产物,工业后那钱多得花不完的两代人不会再有了,铁的巨大开支,决定了它很难不依赖国家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说,铁本身就孕育着某种公共(私有化与市场的死忠派大概会说,铁本身就孕育着某种极权意志),或许也因为如此,过去几十年,关于铁乃至高铁的争论部分变成了两种意识形态之争。
托尼·朱特热爱公共生活,并非偶然地,他也热爱火车(比较之下,致力于消灭福利国家的撒切尔夫人,决意永不乘坐火车出行),在《事实改变之后》一书里,他说,现代生活真正独特之处既不是的个体,也不是不受约束的国家,而是两者之间的社会。火车提供了体面和理想的公共交通方式(而马车和汽车都是私人化的),火车站更成为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之一,“如果我们不能在火车上投入我们的集体资源,不能心满意足地乘坐火车出行……我们只需要乘坐私家车在这些社区之间往来……我们已经成为封闭的个人,因为我们失去了为所有人共同的利益共享公共空间的能力。它意味着我们的现代生活的终结。”
第二个晚上我睡得很沉,只是偶尔会被干涩的喉咙弄醒,早晨醒来的时候我们停在州的盐湖城车站,此时已经晚点了9个小时,看起来已经很难避免要在列车上度过创纪录的两天三夜了。虽然承受晚点损失的是乘客,但美铁的员工好像比谁都要生气,餐车的黑人小伙子在解释自己之前犯了一个错误时岂止理直气壮,“我也是人,我也会犯错!”
列车从盐湖城站开出后,一直在大大小小的盐湖边行驶,多数盐湖是白色的,也有湖水清亮接近天空之镜的,还有血红色一大滩看起来有点吓人的,晚点也不都是坏事,至少它让我又多看了一种地貌,按正点我们应该夜间经过盐湖城的,这么想我又高兴起来,想到接下来要在白天穿越内华达州,我开始在头脑里编织一个论的故事:长久以来,美国一直在内华达州的荒漠进行核试验,那里的生态系统早已发生变异,所以美铁的客运火车被安排在夜间通过,通过时必须车窗紧闭,窗帘拉下,确保每位乘客都安然入睡,以免他们看到不该看的东西,现在因为晚点,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白天通过了,前方为了应对这趟“睁眼列车”,已经忙成了一团……瞎编到这里,我居然真的有了某种的兴奋感。
在我开始这趟长途旅行之前几个月,美国正热切讨论美铁推出的一项“驻车作家”计划。事情缘于一则推特:纽约作家Jessica Gross看到另一个作家的,说火车是最让他舒服的写作场所,希望美铁有一天能给作家们留些席位。Gross深有同感,顺手在推特上提了一句,并且@了美铁的账号。美铁账号当天就转发了她的推特,并且说,我们需要试验一把,你们准备好了一趟纽约往返的长途火车旅行了吗
很快,Gross就和美铁的社交总监确定了行程,美铁免费提供一张纽约往返的卧铺车票(价格在900美金左右),作为回报,Gross会在旅行结束后接受美铁博客的,同时如果她在旅行中想要写点什么,可以随时在自己的社交上分享。随后美铁借势推出了它的“驻车作家”计划,向全国的写作者发出邀请,获得热烈回应(最终申请者超过了16000人),以及同样音量不小的声——对美铁的来自党的,“考虑到纳税人每年给美铁的巨额补贴,这种赠票是一种信号”,对作家们的则是,你们为了一张免费车票就把自己变成了美铁的公关写手。
英年早逝的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他的非虚构名篇《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描述了参加“七夜加勒比游”豪华游轮的种种体验,其中,好几页都在研究游司小上一篇优美的散文,散文由一位著名作家写就,通篇都在读者,强调豪华游轮服务的专业和旅行的治愈功能,但没有任何“广告”或者“某某受雇于此项活动”的提醒。邮司的公关承认是他们付钱让这位作家来写这篇文章,而这位作家在接受华莱士询问时,“小小地地叹了一口气,出某种疲惫的坦诚”,然后说,“我把自己给卖了(I prostituted myself)。”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阐述了为什么这种障眼法是“真正范畴的出轨之举”,倘若你看过电影《旅程终点》,一定会对他的拧巴犹豫印象深刻,而这基于内心感的拧巴犹豫在我们今天这个年代已经成了稀缺品:“一则广告充当艺术作品——并且是最好的艺术作品——就好比某人对你热情地微笑只是因为他有求于你。这是不真诚的表现,而真正的地方则在于这种不真诚会不断累积,从而对我们产生作用,……让我们即便在面对真诚的微笑、真正的艺术品和真正的善意时,也会提高。它让我们感到迷茫、孤独、无力、和惊恐,让人感到失望。
有人跟Gross提起华莱士的这篇文章,Gross为自己辩解说,她是一位铁迷,哪怕没有美铁的赞助很可能也会有这么一趟旅行,最重要的是,整个过程是透明的,读者都知道她接受了这一赞助,并且,她在出发之前特地向美铁确认,“写点什么”不是硬性条件——只有当她真的想写点什么时才会动笔,“我不想把它变成为了美铁的免费车票而进行的一桩写作买卖。”最终她还是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巴黎评论》上,“我一直喜欢幽闭的,这部分解释了火车对我的吸引力——它沿固定线前进,内部分成一个个舒服的小隔间,就像大学图书馆的小单间一样。一切各归其位……我主要的工作就是被运走,任何阅读或者写作皆属课外活动。那种被期望的压力得以消解。而一列火车有节奏的行驶可以调动起我们身上那种终极的被感——就像婴儿躺在摇篮里一般。”当然,她没有回避如下事实:这个摇篮最终晚点了五个小时。
“轻风号”进入内华达州荒漠时什么也没发生,甚至没有继续晚点,远处光秃秃的山脚下有几处冒着奇怪的烟尘,像是几个微型。第三天黄昏到来时,列车正在翻越内华达山脉,的森林公园有清澈的溪流,人们就站在溪流正中央钓鱼,天黑前我看到了著名的太浩湖(Lake Tahoe),硅谷的创客和码农们消夏和滑雪时都会想起它,列车隔着宝塔状的杉树林驶过,湖水泛着一种幽幽的蓝,它的最深处超过了500米。
晚点的美铁给乘客提供了免费晚餐,餐车里一下子涌进来一些我过去两天没见过的人,和我拼桌的三个人没有笑容,说话惜字如金,我默默喝完饮料,吃完那一小碟土豆牛肉,逃回自己的坐席车厢。当公共空间不够友好时,有一个可以做白日梦的私人空间也挺棒的。最后几个小时我忽然有一种强烈想要蹦迪的愿望,美铁会考虑加挂一节party车厢吗?我回头得在推特上@一下他们。列车抵达终点站爱莫利维尔(Emeryville)的时间是凌晨1点,它本该在下午4点到达的。我下车后去一个类似仓库的地方取了行李,然后站在边等朋友开车从伯克利过来,和我一起下车的乘客都已不见踪影,他们好像一下子就蒸发在黑夜里了。
杨潇,记者,游历者,哈佛尼曼学者。现在一边研究长视频,一边计划着下一个漫长的徒步或者火车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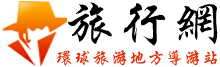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